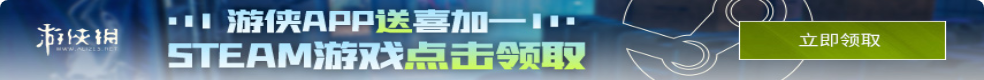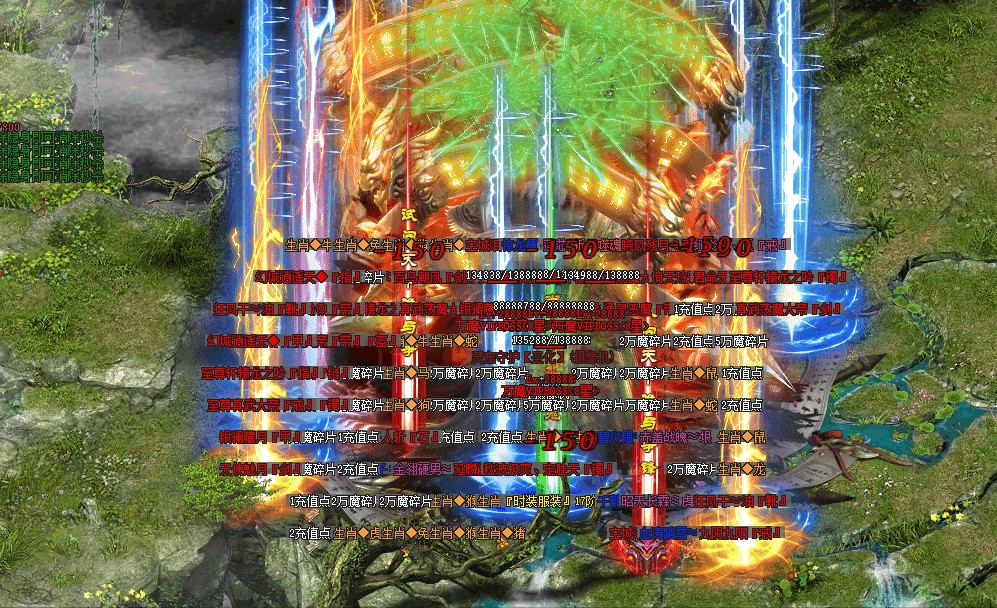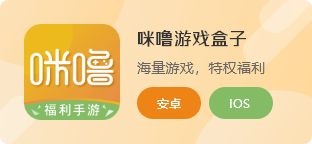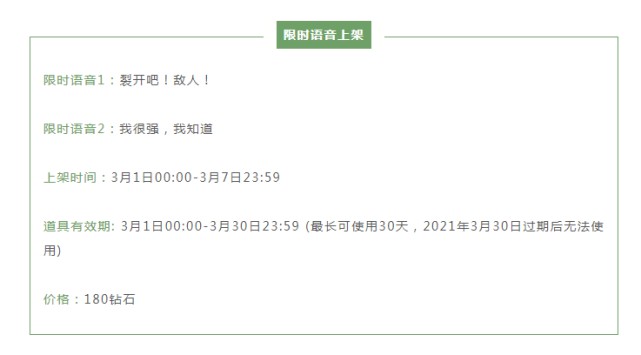深秋的大别山裹着层薄霜,英山县殡仪馆的铁门刚推开,风里就飘来野菊花的清苦香。11月1日清晨,近500人挤在告别厅外的梧桐树下——有人攥着揉得皱巴巴的感谢信,有人抱着用报纸裹着的青菜,还有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举着幅蜡笔画,画里的警察叔叔蹲在地上,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“袁叔叔”。他们要送的,是金家铺派出所所长袁创,那个总穿着洗得发白的、皮鞋后跟磨得发亮还开了胶的“袁老弟”。

10月27日凌晨3点,袁创在派出所备勤室的折叠床上突发疾病。同事发现他时,手里还攥着半本调解记录,笔帽没盖,字迹上沾着他习惯咬笔杆的牙印。手机屏保是女儿去年的生日照,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辅警小桂的:“明天早8点,带两块电池去龙珠村,王防走失手环快没电了。”
整理遗物时,小桂翻出袁创的衣柜——里面除了就是几件旧T恤,最扎眼的是那双黑皮鞋:鞋头裂了道半指宽的缝,后跟的胶边翘起来,鞋帮上还沾着上个月帮王大爷搬化肥蹭的黄泥。“去年所里发新鞋,他说‘我跑村路多,旧鞋软和,新鞋磨脚’,结果那双新鞋至今还在柜子里,标签都没拆。”小桂红着眼眶说,袁创的鞋从来“活”在田埂上,不是沾着泥,就是磨着泡,“他总说,‘鞋跟群众的路贴得越近,心就离群众越近’。”
2008年从警时,袁创是草盘地派出所的“菜鸟”,第一次出警是调解两户人家的宅基地纠纷。他蹲在田埂上听了三个小时,最后把自己的保温杯递过去:“都是邻居,抬头不见低头见,咱们把边界画清楚,以后还能一起搭伙摘茶叶。”从那以后,“蹲下来听”成了他的“招牌动作”——调解婆媳矛盾,他蹲在灶边帮着烧火;处理家禽被盗,他蹲在鸡圈旁看脚印;连帮老人找丢失的耕牛,他都蹲在山路上啃馒头,跟路过的猎户打听消息。
2021年调到金家铺当所长,袁创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所里的“接待室”改成“唠嗑屋”。他搬来一张圆桌,摆上自家腌的萝卜条:“群众来办事,先坐下来喝口茶,把心里的话倒干净。”三年里,他走遍辖区27个村,笔记本写满5本——“张大爷的高血压药该买了”“李婶的孙子上学要过没护栏的河”“龙珠村留守儿童周末没人管”,每一条后面都画着勾,勾满了,就意味着“这事办好了”。

袁创的“微心愿码”,是金家铺的“民心密码”。扫一下,就能把“想要副老花镜”“需要人帮收玉米”“孩子想要本课外书”的小心愿传上去。他每天下班前都会翻一遍,再分给民警:“这些事看着小,却是老百姓的‘心头大事’。”

去年冬天,72岁的陈奶奶扫了码,说“想看看深圳的儿子”。袁创立刻买了智能手机,手把手教老人视频通话——当屏幕里出现儿子的脸时,陈奶奶抹着眼泪说:“袁所,你比我亲儿子还贴心。”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跑十几里路办户籍,他组织“流动户籍室”,每月开着警车进深山,车后厢装着打印机、热水瓶和饼干:“老人饿了垫垫肚子,冷了喝口热乎的。”去年春天,他给91岁的周太婆办身份证,老人摸着他的说:“我活了一辈子,从没见警察到家里办事。”

袁创的“笨功夫”没白费:2024年,金家铺电诈案件下降42%,刑事案件下降20%,龙珠村保持30年无刑案;所里的荣誉墙上,挂着“2023年度综合先进单位”的牌子,下面贴满群众的感谢信——有小学生用拼音写的“谢谢袁叔叔”,有老人用毛笔写的“人民好警察”。
可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了。告别仪式上,6岁的小宇举着蜡笔画哭:“袁叔叔答应带我去看警犬的”;卖水果的陈叔举着“袁所长,我们想你”的纸牌,他的摊位曾被小偷光顾,是袁创蹲了三晚抓住人;70岁的周婆婆捧着一筐土鸡蛋,说“袁所凑钱帮我孙子交了学费,这鸡蛋是给他补身子的”。
告别厅里,袁创的叠得整整齐齐,旁边摆着那双开胶的皮鞋。风掠过挽联,“十七载扎根基层,一颗心装着百姓;四十岁英年早逝,千万人记着姓名”的字迹飘起来,像他生前走村串户的身影。

有人说,袁创没做过“惊天动地”的大事。可金家铺的老百姓都知道,他蹲在田埂上吃泡面的样子,帮老人挑水的样子,穿着开胶皮鞋走村的样子,早就刻进了每一条山路、每一户人家的门槛里。他的“微心愿码”还在更新,“流动户籍室”还在进山,“唠嗑屋”的圆桌上,依然摆着他腌的萝卜条——那些被他温暖过的人,会把他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:“从前有个警察叔叔,用一双开胶的鞋,把每一件小事都做成了‘民心活碑’。”
风里的野菊花香更浓了,告别厅外的梧桐叶飘下来,落在那双开胶的皮鞋上。这双鞋,没走过什么“高光路”,却踏遍了金家铺的每一寸土地;没沾过什么“荣耀泥”,却沾着最暖的民心——就像袁创说过的:“当警察的,把脚踩进泥里,心才能贴进老百姓的心里。”
袁所长,一路走好。